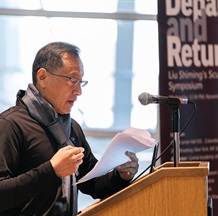进入21世纪,各民族都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化交流日渐丰富与艺术形式日趋多元化的当下,重新将刘士铭及其雕塑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讨论话题的意义在何处?事实上,刘士铭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与研究历程为当下的中国艺术提示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现代性之路。这种现代性叙事,要求艺术家“向后看”,从历史的文脉中去汲取养分,从而孕育出契合不同时代的创作思路。而当这种立足于民族自身文化的中国现代叙事被置于西方的语境下,其将会产生的思维上的碰撞与交流,正是“刘士铭雕塑艺术国际巡展”项目所要探求的方向之一。
2019年10月28日,展览“出走与回归:刘士铭雕塑艺术展”在美国亚洲文化中心(纽约)启幕。为深化对刘士铭雕塑研究的意义与展开由刘士铭雕塑作品出发的而带来的一系列讨论,展览相关论坛于2019年11月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
纽约站是“刘士铭雕塑艺术国际巡展”项目落地的第一站,其作品的选择以及展览的构架都呈现出一种对刘士铭艺术生涯的系统性回顾与梳理。通过论坛中相关议题的提出与讨论,刘士铭艺术中值得被放置于国际文化语境中去持续挖掘与传承的特性逐步显露。当多元文化与多方视角在此交汇,催生出的是对刘士铭特有的“中国做法”式的雕塑创作背后的内心力量与精神共性的深度挖掘,从而为第二站华盛顿展览的启幕埋下了伏笔。
由此,笔者意图从以下三方面来回顾刘士铭雕塑展纽约站的呈现以及展开对其雕塑艺术现代性的认识。
一、“出走”与“回归”:刘士铭之创作历程回顾
“我的一生历尽坎坷、颠沛流离,追求生活,热爱黄土黄河的风土人情和山陕地区的窑洞人情风俗,心想神往,最后来到中原经历十年体验生活中真实的劳动人民的爱和喜怒笑骂,赤赤裸裸地表达她们的感情和爱心。”(刘士铭,1998)
刘士铭在自叙中用了上述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与追求:虽然历经坎坷、颠沛流离,但是一直追求着真实的生活;虽然十余年间远离了繁华的京都,但是在黄土、窑洞与中原地区,体味了人间的至情至性、生活的真善真美。
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红梅系统地对刘士铭的艺术生涯进行了梳理。刘士铭于1946年至1960年在国立北平艺专学习雕塑,是当时第一批、也是唯一一个被录取的学生。在校期间是他接受并积累西方雕塑传统的阶段,5年的研习使他集法国的学院派古典主义雕塑修养和罗丹的具有现代性思想的雕塑与一身。雕塑《丈量土地》作为他的毕业创作,不仅获得了一等奖,还在随后被捷克国家博物馆收藏。紧接着在1958年,他的《劈山引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当时他年仅32岁。因此,国家定件应接不暇,他参与了非常多的国家关于光辉历史、宏大叙事,以及英雄造像等大型公共雕塑项目。应当说,此时刘士铭以及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仅成为了中国50年代的时代形象,也在国际上拥有一定影响力。
然而,在巨大的荣誉与成就面前,刘士铭选择“出走”。他跟随着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到偏远乡村、去到社会底层人民中间,去寻找自我创作的母题。他的足迹踏遍河南、河北,与最困苦与最底层的人生活与交流。在刘士铭眼中,他们尽管贫穷、粗野,可是那样的真实可爱;他们即便生活在封建、落后、守旧的地区,但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都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了刘士铭的脑海中,他需要一种语言、一种容器来承载、表达它们。
1974年,刘士铭为把户口迁回北京与家人一起生活,在保定群众艺术馆办了"病退"。他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进行对中国历代珍贵文物的修复及复制工作。这本是刘士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创作而做的一份工作,却成为了他找到自己独特艺术语言的关键经历。他开始回归到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中去,并在历代泥塑、陶塑中看到了这些作品中所使用的“捏”与“塑”这样的手法中蕴含的情感性与连结性。正是在这个阶段,他走出了一条极为独特的、立足于中国本土文脉的雕塑之路,即他自己命名的“中国做法”。
上世纪80年代起,积累了大量母题素材与逐渐明晰了艺术语言的刘士铭来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爆发期。从1981年到2006年,他的创作又有两个阶段之分:一个是他再次回到母校任教,成为小电炉的守护人;另外就是他回归家庭温暖,退休后在家继续创作,直到他2010年逝世。
刘士铭的雕塑创作历程是独一无二的。他接受的是西方雕塑传统的教育,然而也正因为熟悉,他远离了西方技法,转而在中国传统文脉中去寻找足以承载与传递普通民众最质朴与纯真情感的手法。“中国做法”或许指的不仅仅是来源于塑像传统中的捏、塑等手法,更在于它是生根于中华文化传统,绵延而成的一条连接人世百态的纽带。
刘士铭雕塑艺术纽约站的展览,抓取了刘士铭人生旅途中的两次关键性抉择作为线索,即“出走”与“回归”,以此来梳理刘士铭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品与相关文献。对刘士铭来说,“出走”的游子,放下的是京都的繁华,是已有的荣光,是接受到的西方雕塑语言体系,是一眼望得到头的既定命运。然而刘士铭从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出走”的旅程中,他一路上追求的是真实的情感、向往的是赤诚的生活。而刘士铭的最终“回归”,则是他带着十余年间对生活的真切感受,他急于找到一种刘士铭式的艺术语言来作为容器,去承载他太多的所见所感,于是他在雕塑技法上实现了民族民间传统的回归;而晚年他的创作用陶塑作品寄托对家人的情感与眷恋,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他的“回归”亦表现在对家庭生活以及个人情感上的回归 。
二、“你可来了”与“我来了”:刘士铭其人
“人的一生能脱生为人是很难的,能得到一次生命机会正如半空中一条线串过空中的一个针眼,其难可想而知。”(刘士铭,1998)
“二鬼”是刘士铭的外号,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兄弟们给他起的称号。刘士铭自小便患有小儿麻痹症,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马路教授认为,正是这种对孩子来说地狱一般的经历,才让刘士铭不惧怕地狱的形象,反而渴望了解与认识送葬出殡的水陆画和纸人纸马。少年时的刘士铭喜欢去东岳庙看泥胎神象,在他的回忆中,除了庙里的鬼神塑像,他对“你可来了”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印象深刻。东岳庙里的这四个大字,透露出的是人在死后面对地狱审判时的无可奈何。人固有一死,死亡面前,有人恐惧、有人呆滞、有人浑浑噩噩,而刘士铭回答:“我来了。”一派坦荡从容,并非他没有对生的念想,正相反,他太知道“好好活着”的美好与价值了,他是问心无愧,无所畏惧,所以能坦然面对既定的命运。
刘士铭之子刘伟在《二鬼万岁》一文中,回忆说“他(刘士铭)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治疗自己的方法——他时常给自己开药方,连他父亲都管他叫刘大夫。”刘士铭的命运,或许在小时候就被定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寻求一切治疗自己的机会、锻炼自己;他也努力训练自己的眼睛,因而他能够捕捉到微弱的变化,从中体会形象的个性。
他喜欢和真实的人呆在一起,对别人给予细小的帮助都会感动、记在心里。刘士铭对生命的热忱与他在中原地区十余年的际遇相交织,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母题;而他对死亡、地狱形象的坦然与兴趣以及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经历,则让他在寻找艺术语言的征途中,回溯了根植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表达与技法,这使他找到了承载他情感与艺术形象的容器。
刘士铭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人性”,或是得益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与颠沛流离的际遇,或是因为他在一生的旅途中一直在思考着生与死。这种“人性”贯穿于他各个系列的作品中,在传统塑像的“捏”与“塑”的语言粘合下,在上千度的炉温烘烤下,传递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温度。
三、“神”游纽约:刘士铭雕塑之共情性
“我的小雕塑是生活情感的寄托,而不是雕塑造型的表面。”(刘士铭,1998)
刘士铭立足于传统民间塑像的陶塑是否能够被以西方视角所接受?刘士铭的艺术传递出来的民族现代性能否引起跨文化、语言的共鸣?当刘士铭的雕塑与“中国做法”来到世界当代艺术汇集的纽约,其延展出来的话题或在于对刘士铭雕塑艺术中的当代性与世界性的探讨,由此亦可展开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方向之可能性的探讨。
此次纽约亚洲文化中心的展览以及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学术论坛,汇集了从刘士铭雕塑艺术出发而延伸到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做法”、中西雕塑材料与技法对比、中西雕塑母题与情感以及现代性等多种议题的丰富讨论。
来自法国的视觉艺术家Aima Saint Hunon曾在景德镇有过接触陶塑艺术的经历。亚洲文化中心的展览,是Aima与刘士铭雕塑的首次接触。在她看来,刘士铭的雕塑能够传递出中国人特有的灵魂。他以陶土为介质,表现的是自己以及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内心写照。刘士铭的雕塑题材似乎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他通过作品向观者展示了中国这个民族的文化与性格。陶土是最为朴素与原始的材料,它来自大地,因而创作者能够在使用它的时候赋予其最直接的情感表达。陶土在刘士铭手中成为了传递与向往自由的介质,其作品传递出的人本主义精神跨越了语言、文化与场域,传递给了世界各地的观者。
而来自意大利的Dionisio Cimarelli与刘士铭作品的邂逅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彼时Dionisio通过朋友的介绍,在河南开封了解到了刘士铭的作品。同样从事雕塑艺术实践的他在那时便感受到了与刘士铭雕塑艺术中的共鸣。刘士铭并不是仅仅将陶塑作品视为转化为另一种材料的草稿或是模型;恰恰相反,他在认真思考陶土这种介质本身的特性能够与最终的成品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在他的作品中人们看不到过于繁复的装饰,他在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雕塑本身的灵魂。Dionisio同样认为刘士铭在创作时所选择的材料陶土虽然廉价、随处可见,但它往往能实现很多精彩的情感表现。从刘士铭的创作母题与技法中,能够很直观地体现中国文化的传统——不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工艺,或是埋藏于中国人血液里的亲情关系。
也许正如马路教授在论坛中谈到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推崇刘士铭的雕塑,是因为他完全摆脱了我们过去的那种概念化。从题材上看,他的很多作品可能是跟别人是重复的,但是他的感觉是他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内容并不是题材,而是作品给我们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才是视觉艺术所能提供的最佳内容。正因如此,刘士铭雕塑能够给西方艺术视角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造像艺术技法的介入,更是一种能让观者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去感受他对艺术的赤诚以及雕塑中蕴含的人性温度的力量。
事实上,西方的雕塑艺术除了传统纪念碑式的雕塑外,随着当代艺术思潮与理论的发展,当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念被提出,当马修·巴尼的实验性雕塑不断与各种艺术媒介对话,“雕塑”仿佛正在成为艺术家思想传递的容器。在这样的语境中,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共情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是刘士铭的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一大特性。这也正是刘士铭的雕塑艺术不论处在哪个时代、任何场域,都能为自己发声的“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的力量在于,即使这样的一种极具中国民族特性以及反映中国文化情感的雕塑被呈现于西方场域中,它的民族性也并不会受到题材、形制多样的西方当代雕塑艺术的影响,反而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引导着西方的视角来主动阅读“中国故事”。
纽约站的展览结束于在西方语境下,对他作品中人文精神与人性温度的发掘。而这一议题正将作为其接下来在华盛顿站的展览的主题——“仁者爱人”。作为中西方文化与观念的契合点,刘士铭的艺术精神在西方语境中的认识与发现,将会被更丰富而具体的展开。
现场图片 | 祁思阳,卢唯佳 相关资料致谢主办方